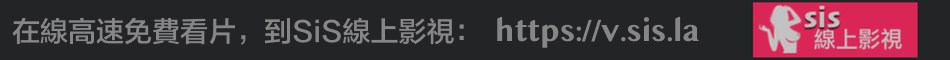小夜曲
各型的汽車、電車穿梭般東往西來,人群擁擠著,高軌及地下線的火車,整日夜轟隆個不停。
夜來時,則更是熱鬧百倍,霓虹燈如彩霞般在彌漫的空氣裡閃耀著,歌聲、酒氣以及各種化粧品的香味,則更令人對於文明社會人類驕奢的享樂生活起著由衷的欣羨。
香港雖也高居在國際水準之上,但與目前擁有一千萬人口的東京相比起來,便有著明顯的不同。
這一晚,我一直被東京一切囂亂的景象所引誘,直逗留到將近黎明時方被一位木村先生領至一家小型的觀光旅社休息。
第二天,我甫在床上大伸懶腰剛準備起身梳洗的時候,僕歐便送進一張印有「東京失蹤人口調查局」的萬鵬先生的名片。
他是受了香港的委託,來調查我的下落,並送來一張署名張良人的化名電報給我。
拆開來電,知道千枝又延遲了一天行期,本來,她要在今天下午五時到達羽田機場的。
如此一來,我又要多苦待一天,同時,也將要在這兒多荒唐一天了。
在快樂中,時光便會出人意料地快速地消逝,但惟有在等待某一件事情的發生,或者是在等候某一人物的出現卻是例外。
早知道她要延期前來,我當可以更改班機,而再到辜紅家中去享樂一天多好。
這一天當中,還是那位木村先生義務導遊,引領我大逛東京附近的名勝古蹟,代價是十八元美金。
這時正值櫻花盛開的季節,東京市內以及郊外,遍處一片火紅,壯烈而短壽的日本國花,給人一種狂野的挑逗,尤其是那些風姿嬌柔的日本姑娘,穿著比紙還單薄並且透明的衣衫,那半隱半現的豐腴美好的胴體,則更給人一種致命的刺激。
木村看出我的心事,便以生硬的廣東話對我半開玩笑的說:「你想找個花姑娘開開心吧?嘻嘻…」
「有嗎?」我也生硬地回他一句。
「走!我帶你去找。」
也不徵求我進一步的同意,說著便一招手叫了輛計程車,對那留小鬍子說了一陣,便拖我進車廂裡去。
東京的車輛行人雖多如過江之鯽,但卻非常流暢無阻,片刻功夫,我們便駛到靠近舊皇國府旳街道上來,在將近河畔的兩扇朱紅大門前停了下來。
下了車,木村代付十元車資,便逕自向前去按電鈐,出來應門的是一個身材纖細的芭蕾舞孃型的姑娘,他們相對又是一陣談話,隨後,那姑娘便引我們進去。
一間寬闊的西式大廳,裡面又完全像中國北方書香間第的擺設,穿出進的又是些身著和服的而蓄新款巴黎鳥巢的姑娘,真是不倫不類,叫人發笑。
日本女子侍候男人的體貼、溫馴是舉世聞名的,她們環圍著我,每個人都向我行著九十度的大禮。
當她們行禮時,一股股混著高級化粧品的肉香,便悠然的從開闊地胸領間散放出來,使人如墜香粉罐中,頓時,胸臆間那種狂亂的野性便油然而生。
所謂「劉佬佬進大觀園」,不久便覺眼花瞭亂起來。
還幸虧身旁有個譯者,他見我一時被眾妖所惑而無法定奪的時候,便自動出面給我解圍。
他為我找了個戰時隨父母到中國大陸住過幾年的姑娘來,名叫介子,人大方而又和藹,個性就像菊花那樣的文靜,使人一見便覺得異常的愛憐著。
介子的漢語說得很流利,她的小房間裡也全是古色古香的中國擺飾,四壁掛滿中國山水字畫,並且桌旁還焚著一盤檀香,香煙繚繞,倍增一種如入仙境的神祕氣氛。
她恭敬地以中國話向我問長問短,一面從酒櫃中取出一瓶烈酒,一些糖食水果。
她知道很多的事情,並也知道中國人愛飲烈酒白乾,可是她自己卻是滴酒不沾唇的人。
我在喝酒,她便在一旁笑臉作陪,並不時信手拿些葡萄什麼的往小紅嘴裡送進去。
一番小飲過後,自不必多說廢話,食與色不容分離,自然,接著而來的便是行人倫大禮。
介子先替我寬衣解帶,然後,她自己再緩緩地解脫一光。
「解除武裝」以後,我們便並躺了下來,她兩眼夢樣地瞪著帳頂,並極纏綿向我傾訴她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