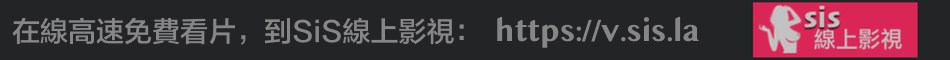夜遊
凌枝趕緊說道﹕「不﹗我年紀雖小,也是女人,晚上和你們同樣難熬,因為我已經並非小孩子﹗牧童們的幾支短笛,總是到喉不到肺,況且剛才是平山先招呼我呀﹗」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在這裡不幹嗎﹕」惠雅又反問了一句。
凌枝小嘴尖尖,低頭說道﹕「我祇不過是說門面話嘛﹗其實有得享受,為什麼不幹呢﹖以前躺在黑漆空棺材上我還幹呢﹗」
「你和羅剛到底幹了多少次呢﹖」春桃忍不住問。
凌枝道﹕「直至他亡故,從未停止遇。究有多少次,你自己計算好了﹗」
目下又是冬天了,羅剛是秋初死亡的。如此說來,羅剛推說去販牛,卻躲在土地廟樂和小鬼頭稜枝偷歡,巳達半年之久。
「好啦,好啦,別鬧了﹗」平山見幾個寡婦都紅看眼睛跟稜枝爭歡,知道個個饑渴透頂。秋菊等有丈夫的也想換換口味,未必肯放鬆。在席的女人全部變成張口欲噬的母狼,倒叫他左右為難。
這時,翠芳突然提出建議,她說道﹕「大家抽簽,分前後次序來玩,豈不時很公平嗎﹖誰先誰後,踫自己的運氣﹗小妹妹,你贊成嗎﹖」
稜枝無奈,祇得點頭答應。經鄭重抽簽後,便把春桃家的廳堂當作陽台,眾人全部脫得一絲不掛,一男數女胡天胡帝,戰鼓冬冬的直達天明。
這裡是山地農村,『夜遊』傳統風俗原封不動地遺留著。所謂『夜遊』即是任何男人夜半摸黑越牆,爬入女子閨房,默然剝其下裳,就軟玉溫香抱滿懷。女子被襲驚醒也噤若寒蟬,聽其飽餐而去。女方無論是含苞處子,抑或有夫之婦,均可不問。
『夜遊者』,踫到肉穴便鑽。如果是容貌醜惡的女人,當然沒有『夜遊者』問津。所以有句罵人話﹕「那個醜八怪,連夜遊者都不屑上門﹗」
常給夜遊者偷襲的少女,人次愈多者愈容易出嫁,少婦亦然,能被多人偷香的,丈夫視作瑰寶、夜遊者當然最喜歡偷姦少女,但往往因門路不熟而誤入她嫂嫂的房間,如果剛巧她哥哥又遠出未歸,嫂嫂便會自動梅開數度,讓夜遊者酣暢享受。次日倘若少女得知,還會對嫂嫂吃醋哩﹗」
不過設若夜遊者偷襲了寡婦,村人們全要冷嘲熱諷,認為他沒有頭腦,是個缺乏靈魂的畜牲,晦氣之星巳鑽進他的身軀,從此決無好日子過了。因此,無論怎樣美麗小寡婦,夜遊者是裹足不前的。
有謂一處鄉村一個例,離此不遠的一個村落,凡是有夫之婦與人通姦,一律以私刑處死。先剝光姦夫淫婦的衫裳,把男女性器套合,用粗繩捆綁,抬著街示眾,然後裝入豬籠棄於水塘浸死。
然而在此,則不禁『夜遊』活動。凡夜遊成姦,男女皆無罪。這種風俗習慣自古流傳到現在,積重難返,不易革除。
平山總算不容易,他徹夜和一群小母狼輪流肉搏,他屢博屢起,讓他們個個聊解饑渴,直到天明後,大家才穿上衣衫,圍坐閑談。
春桃余興盎然,咽了一口唾沫問平山道﹕「你也和羅剛一樣,常常出去夜遊嗎﹖」
「我跟羅剛略有不同,要夜遊總往鄰村,兔子不吃窩邊草嘛﹗」平山眯著眼回答,向火缸裡投進一條粗大的炭,春桃也向炭凝視。既與平山發生關保,便不再畏羞,伸臂直前,把他愛撫欣賞起來。眾人見了,也移坐前來,爭先恐後地愛撫著他的肌肉。
「哇﹗那麼壯實,昨晚輪到我時就急著吞咽,竟不及仔細瞧哩﹗」翠芳說。
「你不知道嗎﹖力猛有長勁呀﹗」人稱伯樂善於相馬,春桃自以為善於相人。
「怪不得他一口氣便打了個通關,都叫我們涕液橫流啦﹗」惠雅口角流涎地感嘆。
「羅剛的還要凶錳哩﹗」小妹妹稜枝忽唱反調,因為她剛才抽簽,竟是最後一個。輪到她時,平山巳成強弓之末了。她覺得不太盡興、難免心有未甘。
「雖然羅剛兇猛,但程咬金三斧頭,怎及平山耐久啊﹗」秋菊說。
「我也認為頭等重要的是耐久,其次才是兇猛,大小倒不在乎。我三個死鬼丈夫之中,第二個雖然陰莖最小,但耐力卻最久,簡直銳不可當,所以我至今仍是特別痛惜他呢﹗」惠雅幽幽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