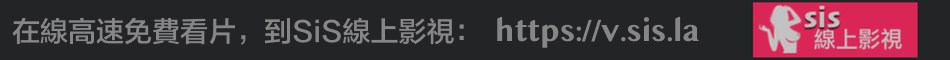兄弟連
他把自行車輻條磨尖,在前端彎出一鉤來,又跑到臭水溝子旁邊挖了幾條又肥又長的蚯蚓,穿在鉤上,帶著我走進正灌溉著的麥田之中。
就見他邊走邊觀察阡陌之下水中的狀況,見有氣泡冒出,就蹲下去,用輻條小心的探試,接著就看他胳膊猛的一震,一條尺把粗的大鱔魚被拽了上來。那一下午我們共釣了四條,全部歸了我,我把魚送到葉胖子那裡用辣椒一炒,乖乖那個香啊!從此之後葉胖子也愛上了辣炒鱔魚。
那年夏天我釣了幾十條,後來小芸說她見了黃鱔就想吐。
我所在的部隊那時自己養牛,牛奶專供空勤灶。養牛的兵是內蒙古人,兩瓶酒就把他搞定了。剛擠出來的牛奶熱熱的,很稠,稍微一放就變成如豆腐腦般的半凝固狀態。蒙古兵說:「你們內地人身體不行,一桶奶要兌半桶水喝了才不上火,俺在家的時候直接咬著母牛的奶頭喝,喝口奶嚼一口乾牛肉。」
我心裡說:「吹什麼牛逼啊,踢死你個小丫的!」離開後勤股後牛奶就很少喝到了。
部隊大院周圍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其實都是部隊產業,早幾年這些地是分給各個連隊耕種的,但每到麥收季節,莊裡的農民就全家出動打秋風,一垛垛往自己家搬。警衛連戰士挎槍站崗根本鎮不住這幫人,他們只怕警察不怕當兵的。
那次一小兵追個偷麥子的農村婦女,那女人被追急了,往地上一躺就脫褲子,嚇的那個小戰士轉身即跑,後來戰備任務越來越重,連隊便將麥田包給附近的各個村子種,每年只須交給部隊部分糧食就可以了。
灌溉麥田的水來自於十幾里之外的黃河,水被抽出後通過大小水渠供應周圍五六個村莊。我們團東大門外就有條水渠,渠不深,水最多時才剛沒過膝蓋。
有次我無意中在河邊經過,發現雖然灌溉已經停止,但焦黃的河水中不時有小魚翻起雀躍,於是趕緊跑回營房股,叫上一幫戰友,拿著鐵掀臉盆衝出來。先將水渠兩頭用泥巴糊住,然後十幾個人跳進去往外潑水,水越來越少,魚越來越多。十幾米長的水渠我們竟撈出大半桶小雜魚,甚至還抓住了一條一斤多沉的黑魚。晚上送到灶上炸了,好吃的不得了。
在幾名廣東籍飛行員的帶動下,部隊興起了打鳥熱潮。一到晚上,周圍的小樹林中就手電筒亂晃,參與者上至團長參謀長,下至剛出新兵連的娃娃兵,所以當時上下級關係顯得非常融洽,看見蹲在樹上過夜的鳥都互相讓:「你先打你先打。」——正所謂「同是連隊打鳥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小陳也買了只氣槍,「峨嵋」牌的,一到夜間我們就叫上葉胖子出來,滿院亂找。飛行隊的那幫飛行員打的最好,有眼力有臂力,四五個小時能打一網兜。打死的麻雀用熱水一燙,毛就好拔了,再放熱油裡炸過,很香。許多年後我調進民航,每天看著一箱箱活蹦亂跳的麻雀空運到廣州深圳,卻傷感的不得了。我的心是越來越軟了,痛惜起這些小小的生命。
當年新兵連裡有個戰友,關係不錯,後來分到了警衛連,每天在跑道周圍站崗。因為是單崗,離營地又遠,他膽子就越發大起來:一到站崗的時候就跑到兄弟部隊的魚塘裡釣魚,有線有鉤有蚯蚓就是沒魚桿,他就把五六式衝鋒鎗上的三稜刺刀拔出,把線栓刺刀上那麼釣,釣上來就揣懷裡直接送大灶上去。
有一回他釣魚時碰巧被那個部隊下來檢查工作的幹部看見了,一頓臭罵,還威脅說要把這事捅到我們團裡來。這個傢伙懷恨在心,下次去時帶了一包砒霜,也不知他在哪弄的,反正全撒魚塘裡了。見到我時還咬牙切齒的罵:「讓他們吃魚,都他媽吃屎吧!」
警衛連確實不是人呆的地方,風吹雨淋日曬領導罵。幹部灶和大灶合併之後他們的伙食算是好了點,一開始他們是吃兵灶的,伙食很差,個個滿臉烏黑,精瘦如柴。
新兵們大都本份,巡邏時絲毫不敢懈怠,站了兩三年崗快退伍的老兵油子們就懶散多了,值勤的時候哪也不去,找個陰涼地兒看武俠小說,有勁沒處使的就用槍上的刺刀挖老鼠洞蛇洞,槍管子裡面堵滿了土,下崗時往地上磕打磕打。再不就找個不留神闖進警戒區的老百姓,打罵一通解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