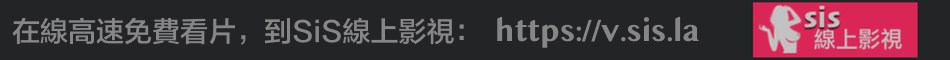兄弟連
再講一個故事:
那年國慶節,部隊放假,葉胖子說他生日快到了,叫上一幫東北兵跑我這喝酒打牌。大家正喝的興起,姜小芸突然闖了進來,兩隻眼睛都哭腫了,跟桃子似的,見了我們哇的一聲又哭了,彷彿老百姓看見了八路軍。
當時大家都傻眼了,我趕忙扶住她肩膀問:「怎麼了小芸?別哭別哭。」
小芸激動得話都說不上來,囉哩八嗦了半天才聽明白:場務連有個北京籍排長,快三十了還沒找對象,最近經常打著看病的幌子到衛生所找小芸,只要沒外人在場就對小芸上下其手,小芸怕我生氣,一直忍氣吞聲不敢對我講。今天這傻逼喝醉後又去了,往病床上一躺說他蛋子痛,可能是疝氣,讓小芸給看看。
小芸說:「我這檢查不了,你到軍區醫院去。」
那孩子說:「總得先做個初檢吧,興許你揉揉就不疼了呢。」
小芸說:「你滾蛋,要不我喊人了。」
他說:「你喊啊,看咱倆誰丟臉……」
幾個東北兵藉著酒勁就往外衝,邊沖邊嚷:「蛋子疼?給你揪下來就不疼了!」
我喝住他們:「都回來都回來,別這樣!」
葉胖子比剛來時沉穩多了,他倚在床上沒動窩,叼著煙說道:「咱們團這些當兵的沒幾個不知道你跟小芸的關係,老程你想想得罪過這個人沒有。」
他這一提醒我還真有了點印象,早在新兵連時我曾和一操北京話的老兵吵過一回,當時確實怕事,戰友一拉架我就見坡下驢的閃了,莫非是那小子?
為這事,我跟葉胖子密謀了一夜,他後來在我那睡的。
葉胖子的一個老鄉在場務連當副排長,愛人隨軍後來到部隊在空勤灶幫忙,葉胖子平時很照顧她,有什麼好東西都不落下她。平時葉胖子也經常往這副排長家串串門,瞭解到一些情況:他當兵十年,副排長就幹了五年半,急著往上爬,但禮送了人也圍了卻總是沒消息,鬱悶的很。葉胖子就說這事找他准辦。
國慶過後沒多久,部隊進行戰備演習,各級指揮員二十四小時待崗,不準離開營房。有天晚上場務連連長在浴室刮鬍子洗臉,順手將剛買的「上海」牌鋼表放在了窗台上,等出來後發現表沒了。不含糊,全連立即緊急集合,放出哨兵守在宿舍門口,任何人不準外出,然後進行大搜查,這塊表後來在那個北京籍排長的抽屜裡找到了,上面還帶著水珠。
這事就是葉胖子那個老鄉乾的,確實是妙計,一箭三雕:我的仇算是報了;北京排長很快被強制退伍,掃地出門;那個東北籍的副排長頂替他的位子榮升正排,住進了單身宿舍。接著這傢伙又逮住機會,立了個「二等功」,好像是「在雷雨天氣帶領全排戰士搶救暴露在大雨中的航材」吧,上了軍報,到我退伍時,他已經成連長了。
為這事我專門請葉胖子喝的酒,可沒叫他那個老鄉來,為什麼呢?他的關係由他搞定,我出面顯得不太好,況且這事人家也肯定不想讓太多人知道。
(五)再次無題
小芸懷孕了,但我一直對她懷孕的原因持保留態度,倒不是懷疑她跟別人亂搞。每次辦事時我都戴套,這些避孕套本來是軍區下發給連隊各級軍官用的,很厚的那種,用半透明塑料紙包著,由於平時都由衛生所發放,小芸就沾了個近水樓台之利,經常偷點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那批避孕套在倉庫裡放的太久,可能讓耗子嗑過。打那之後小芸改吃「探親避孕藥」,不過這東西副作用挺大,吃了之後嚥不下飯。
小芸跑到軍區醫院找熟人打掉了我的第一個兒子,身體很虛弱。我問她想吃什麼,她說就想吃鱔魚,想的不得了。
這可真難住我了,在北方當過兵的朋友都知道,北方人不認這玩藝兒,就說這幾年生活好了吧,吃鱔魚的也很少。附近幾個農村大集我跑了個遍,魚販子瞪著一雙無知的大眼睛問我:「鱔魚是什麼魚?」
前文交待過和我在營房股住一個房間的那個幹事。安徽人,很有點能耐,會吃,每年自己灌香腸做燻肉淹酸菜,每次還都分我點嘗嘗鮮。我把買膳魚買不著內心很苦悶這事跟他說了。他說:「嗨!多大點事啊,我有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