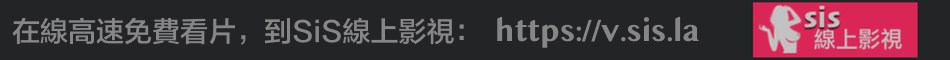嫵媚
「你愛我嗎?」嫵媚輕輕地又問了一句,眼中滿是柔柔的嫵媚。
我的慾火熄滅了一半,琳的容顏該死地浮現於我眼前。
嫵媚軟綿的身子開始僵硬,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我。
我漸漸鬆懈,嫵媚的雙手也放開了,我把手從她內褲裡抽出來。
「你還愛著她是嗎?」沉默了許久後,嫵媚才問。
小時候,父母稍微地責罵就能令我啕嚎大哭,但自中學後,流淚的功能似乎消失了,記得有一次落了單,在馬路上被一幫長年敵對的爛仔圍毆,命差不多丟了半條,也沒掉下半顆眼淚來。
嫵媚搶上來抱我的手臂,哭道:「別剪,求求你別剪。」我看她在乎,剪得更是痛快,千百縷藍色碎布條從空中四下飛散。
嫵媚突然尖叫:「這一件不能剪!」雙手死死的抱住我的手臂。
我乜見在第三顆鈕扣處有一抹暗色的褚紅,冷笑一聲,一剪從當中破開。
嫵媚哆嗦了一下,彷彿我剪著的是她身上的肉,忽然說:「別剪,我以後再也不纏你了!真的。」我停了手,冷冷注視她。
嫵媚悲慟地跪在地上,把那些藍色碎布緊緊抱在懷中,抽噎不住:「你好殘忍,你真殘忍,既然你一點也不愛我,為什麼你那天要來找我?為什麼你那天要背我?」我終於平靜下來,丟了剪子,看見她爬起來對著牆壁,嘴裡猶自喃喃囈語:
「不公平,真不公平。」我淡淡地說道:「從來就不公平,這世上從來就不公平,老天爺從來就不公平。」心裡有一種近乎冷酷的好笑,頭也不回地出門,下樓,絕塵而去。
我知道,今生的藍色階段終於過去了,嫵媚失去了我,我也失去了琳。
四十四、最後的嫵媚
一年很快就過去,我心如止水的工作,寫文章,很少喝酒,沒有再去風花雪月,跟玲玲、阿雅、嫻兒、媛媛的聯繫基本都斷了。
偶爾會在深夜裡接到沒人開口的電話,來電顯示是陌生的手機號碼,後來我就習慣了,接通電話也不問是誰,只是默不作聲地跟對方乾耗著,安靜地聽著彼此輕輕的呼吸聲。
我希望是琳。
這段時間,反而跟一見面就拌嘴的如如聯繫多了些,偶爾會一起去跳舞,聽歌或泡吧,我想從她口中得到琳的消息。
無奈如如總是守口如瓶,被我逼急了就哼忘了是誰的歌:「命裡有時,終歸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某夜的迪廳,我們在舞池邊搖頭晃腦,如如忽然指著某個方向叫我看。
我費了很大勁,才從人群裡辯認出其中一個是嫵媚,她把原本令我感到驕傲長髮剪了,染了一頭十分撩人的玫瑰色,玫瑰色唇彩,黑背心,胸前尖尖的兩點讓人一看就知道沒戴乳罩,下邊一條短短的皮裙,唯獨一雙黑色高跟涼鞋還具本色,正在一幫爛仔中間以一種極盡妖媚與放蕩的舞姿拋撒嫵媚。
我怔怔地看了好一會,見嫵媚下場休息,身子親熱地貼著一個穿著明晃晃藍上衣的小子。
如如說:「是尼格那一圈的。」我仔細一認,就知如如沒有看錯,不禁一陣反胃,那圈人五毒俱全,隨便那個小角色都比從前的我更壞,傳說他們搶劫,砍人,吸毒,還群交。
藍衣小子幫嫵媚點煙,嫵媚跟他親嘴,旁若無人。
我忽然朝她走去,如如想拉沒拉住。
幾個爛仔警惕地盯著我,嫵媚也看見了,吐了一口煙圈,跟他們說:「我朋友。」我對嫵媚說:「聊聊天,那邊。」指了指巴台。
嫵媚居然看那藍衣小子,那小子看看我,目光銳厲,眼神陰鷙,一副輕狂不羈樣子。
我淡淡地看他,見他緩緩點了點頭。
嫵媚跟我去巴台坐,要了一杯dubolgalant,吸了口煙,一手優雅地托著香腮,等我說話。
我看看她頭髮,忍不住說:「難看死了,狗窩似的。」嫵媚瞄了我一眼,說:「難不難看,關你事?」眼睛往那個小子瞟一眼,說:「他喜歡。」「別跟這幫人混一起,你會吃虧的。」我一陣焦躁。
「謝謝,還有什麼事?」我愕然,只感索然無味,發覺嫵媚已完全陌生。
我回自已的位子,「怎麼樣?」如如問。
「只談了兩句,只能談兩句。」我滿懷鬱悶。
如如又說:「那小子的眼睛很厲害。」「厲害個屁!假的,裡邊沒內容,藍色早已過時了,現在還穿著晃,整個廳裡就他就最扎眼,扮酷且沒品位。」不知怎麼噴火似地一下子吐了這麼多,心中一陣無比複雜的感覺:嫵媚墮落了。
如如喝了口酒,看了我一眼說:「想不想聽我的感想?」我不認為她能有什麼高見:「隨便。」「說實話,其實那小子像你,像從前的你,簡直就是一個模子裡打出來的,而嫵媚,她像那個阿雅,你以前的那個阿雅。」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嫵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