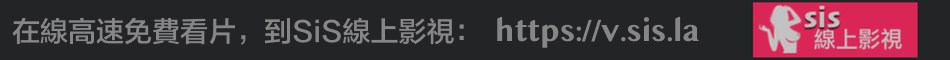考後三步曲
- 分頁 1 /11
- 下頁
早上,我被一陣鐵質工具敲打木板的聲音吵醒了。
我沒有動彈,仰麵望著在天花板上懶洋洋地打轉的兩隻蚊子,肯定在昨天晚上吸飽了滿滿的鮮血——我那麼累,睡得那麼死。
我就這樣躺著,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今天是高考後的第七天。
外麵,整個城市的喧鬧聲開始在遠處活躍起來,鐵質工具敲打木頭有規律的聲響就在窗口下方的庭院裏,尖銳而刺耳榔頭敲打聲,伴隨著來來去去的腳步聲充滿了我們呢之間沉寂的空間。
公園的山頭上泛起了魚肚白,亮晃晃地一片,太陽就要從那裏升起來了。
最後我還是從床上起來了,找了條內褲穿上,趿著拖鞋「踢踢踏踏」
地走到窗戶邊伸出頭去,想看看究竟是誰這麼大清早就忙忙碌碌的?庭院的空地上,有一大塊長方形的細木薄板,朝上的這一麵刷著白漆,光滑可鑒,性吧首發一邊放著參差不齊的方木腿子,像是從廢棄了的桌椅板凳上卸下來的,上麵還有鏽跡斑斑的尖銳的鐵釘。
房東蹬在這對亂七八糟的木頭前麵,背朝著我這邊,揮舞著鐵錘和這些鐵釘努力地戰鬥。
房東的後腦勺就像長了眼睛,蹲在地上扭頭朝窗口看了看,「嘿!嘿!」
她朝我擠擠眼睛,裂開嘴呵呵地笑起來,「你愣著幹嘛呢?我正想叫你,原來你已經起來了,快下來幫我的忙!」
她扔下鐵錘站起身來,兩手叉在腰上活動一下,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
「等等,」
我說,「我還沒洗臉呢。」
我穿好衣服到陽台上的水池去洗臉。
雖然在這裏住了將近半載,和房東的交流也不過見麵點頭微笑,連她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也沒有寫什麼租房合同,她隻是每個月月末按時來收一百塊錢的租房費和水電費。
不過總的來說,她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
我下得樓來,房東又蹲在地上埋頭幹活,她今兒穿了一件曳地的黑底碎花長裙,頭髮胡亂地紮在後麵,略顯得蓬鬆淩亂,腳上穿著一雙厚底的棕色草編拖鞋,整個人顯得樸素,但很有審美感。
尖利的「叮當」
聲使得她沒有注意到我已經走到跟前。
「你在幹嘛呢?」
我站在她前麵問她。
「來了,」
她抬起頭來,臉上閃過一絲驚慌,仿佛吃了一驚,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這可麻煩你了……」
她說著站起身來,「哪裏?不麻煩,」
我連忙笑著回答,「反正我也閑著沒事,把錘子給我。你這是要幹嘛呢?這麼大清早的。」
她把鐵錘遞給我,我才發現她的手指纖細而白嫩,性吧首發不像是一般的家庭主婦的手,那種手雖然也很光滑,但是看起來就像被油汙浸泡過的,不是這種自然的白,我幾乎懷疑她是否也做家務,「把那些釘子弄出來,」
她說,「這不,孩子放暑假了,非要一個乒乓球桌,她老子年前就答應他了,現在還沒弄好,孩子從昨天就開始生氣呢,一大早非要做好。」
她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
「小孩子嘛,都這樣的。」
我說,朝門口看了一眼,看見那小家夥嘟著嘴坐在沙發上,臉上還掛著淚花,眼睛卻直溜溜地盯著電視上的動畫片。
「是爸爸答應孩子的,怎麼不叫爸爸來弄?」
我蹲下來開始幹活,我隻知道房東有一個六七歲的兒子,周末才從學校回來,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丈夫,就連她自己,我們也不是常常見到,除了收房租的時候。
「唉,他爸爸一年到頭都在外麵打工,除了過年的時候回來一個月,哪有時間給它弄這個玩意?」
她理了理貼在額頭上的發絲,後退幾步在我對麵頓了下來,把裙擺扯過來夾在膝蓋間遮住,「不錯啊,小夥子,」
看到我很快就從木頭中拔出一個釘子,她讚賞地說,「還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我這記性,老是把你們的名字搞混,你知道,住了太多的人。」
她歉意地說。
「我叫譚華,叫我阿華就好,」
我說,把釘子放到一邊,翻著木頭尋找下一顆釘子,「拔釘子不能蠻幹,像這樣,用錘子扣住,下麵地主,往後一板,不是往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