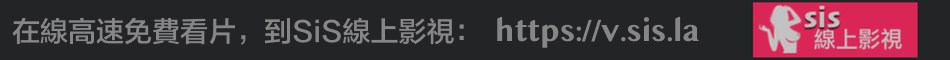女兒的援交
錢交她了,要做的經已做完,我應該裝作上廁所然後暗中離去,對雪怡來說這有利無害,她會感到奇怪,但不會介意。沒有一個援交女不樂意在收錢後什麼也不用做便讓她走,包括我的女兒。
還是我應該在這時候表露身份,跟她說爸爸什麼都知道了,妳有苦衷跟我說,我們一家人,永遠共同進退。這也許會刺激到雪怡,但總好過讓她繼續當一個人盡可夫的妓女。
可是我沒有,眼前這不認識的女兒留住了我,她留住了我的心。嫵媚的笑容、誘惑的聲線,充滿女人味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我從未見過。我甚至以為這只是一個跟雪怡人有相似的女孩子,是一個相似得連父親也無法分辨的女孩子。
「伯伯你都不說話呢,對了,你不想給我知道身份,明白的,那你什麼也不用講,好好享受飛雪妹妹的服務就好了。」雪怡親暱的挨著我說,女兒很聰明,遵守當日的承諾,配合我不希望暴露身份的要求。
這不是女兒第一次挨在我身,蹦蹦跳的她總愛撒嬌地撲入我懷裡,但從未試過如此嬌美動人。我直覺整個人像被層層鐵鏈鎖在座椅上無法動彈,只能眼白白看著雪怡接下來的演出。我知道這是身為父親不可以接觸的事,內心最深層的惡念,卻慫恿我去接近這可怕而又有著魔鬼甜美的誘惑。
『不…雪怡…我是妳爸爸…我們不可以…』
我寧願雪怡是一個女騙子,騙財後就用各種藉口逃之夭夭,不會對那些陌生男人進行什麼服務,可惜這個唯一的願望仍是落空了,女兒不但沒有逃跑,還表現得像個敬業樂業的熟練援交女。
雪怡端正地坐在自己座位,安靜觀看了五分鐘的電影,手開始徐徐地伸過來,隔著長褲在我的大腿上輕掃。
『…她…雪怡…要開始了…』
那是一種放鬆整個人繃緊的撫摸,輕輕的,柔柔的,沒有半點侵略性,是慢慢挑起情慾的前奏。指尖在大腿上每吋遊走,覆蓋整個範圍,偶爾來到內側,在快要到達敏感位置前便立刻離開,偶爾又會裝作不經意地觸碰到重要部位,每次都是蜻蜓點水,一碰即止。
這是一種最高級的挑動人心手法,叫人巴不得纖纖玉手,立刻便使勁地碰在關鍵位置。偏偏雪怡沒有使你如願,而像來日方長的故意放慢步伐,欲擒先縱,一步一步地把對手勾進她的指頭上。
我知道雪怡開始她的工作了,這種時候我應該制止她,不讓壞事情發展下去。
但男性本能叫我沒法自己,女兒挑逗的技巧使人著迷,我無法抗拒眼前慾望。因為一時之快使悲劇發生從來是千百年來男人的劣根性,每個男人都會做錯的事,如今在我眼前進行。
『雪怡…』
焦躁在體內升溫,陰莖開始膨脹,逐漸在褲襠上形成臃腫一團,對再一次因為親生女兒產生性慾我感到羞愧,雪怡像嘲弄我的醜態般發出半聲嬌笑:「嘻嘻,伯伯升旗了呢,可以給我摸摸嗎?」
這是不用回答的問題,事實上女兒亦沒待我反應,小手緩緩放下,像初次撫摸男人器官的輕輕接觸。感覺到陰莖被觸碰時我不自覺地輕嘆一口,被女兒觸碰下體的感覺原來非常好,我不知道這是否出於亂倫的刺激快感,如果面前的不是雪怡,我想就是更優勝的美女也不會有這種興奮。
『雪怡…在摸我的雞巴…』
雪怡摸了一下,嘟一嘟嘴,再摸第二下,第三下,像愛惜一件心愛寶物的柔柔細撫,撫摸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隔著褲子完全洞悉陰莖的虛實。她以指間比劃,在我耳邊小聲說:「伯伯的小弟弟有七寸呢,很長,是大雞巴哥哥。」
讚美的說話使人飄然,從女兒口中聽到雞巴這低俗話亦是有種莫名興奮。雪怡繼續細摸幾遍,看到陰莖愈發脹硬,取笑我說:「伯伯不乖呢,飛雪妹妹給你教訓的。」
說完五指纖纖,落在兩腿中間,像啄木鳥以指頭輕輕啄食那正被注入血液的器官。一啄、兩啄、三啄,整支陰莖便昂然起立,直豎在最矚目的位置。
雪怡壞笑著說:「哎喲,伯伯紮起帳篷了,好大的一根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