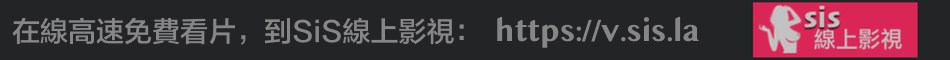櫻花綻開時
- 分頁 3 /3
- 上頁
我與她是男女朋友了。以女友的感覺來說,她是個好女友,除此之外,有個日本女友的好處是:幫助你在日本的生活多開了一扇窗。她會告訴你原宿的那條街最熱鬧;會指點你銀座的三越百貨在那兒;會幫你向日本的衙門交涉;會教你課堂上也學不到的日語。當然,做愛時的嬌嗔也是日本女人式的。
我在沒課時,必定直奔橫濱;每到橫濱,必定數日不歸,凡此已成常態。同學們,包括日本同學在內,都羨慕我的好運,直說我在日本的生活過得最愜意。
然而,事情卻不是一直都是如此順遂。
回想起來,我與她一路走來,似乎毫無波折。從認識到成為男女朋友,幾可用快如閃電來形容。與她的交往,早已不曾意識到國籍的存在。「你回國的話,我也要跟著你走。」她已不只一次地向我這樣表達過。
與她走在原宿的商店街上,在她挑著店內裡的商品時,我故意走到店對面的一個角落,遠眺著她的身影。天啊,她真的好美。我是喜歡她的,在這熙來攘往的人群中,要我重新再選擇,答案仍是一樣。
那個自認識她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問題,如今再度浮現,而且更嚴重:將惠的爸爸已到了病危的階段。十一月起,她不得不由橫濱住處趕回川崎市家中。我們有整整一個月不曾見面。這一個月,我們靠電話與書信聯絡。她那住在川崎市的母親也已知道我這個人的存在。對於她的女兒與外國人交往,她是堅決反對的。若是收到我的信,她也是冷冷地對將惠說:「妳的那個KOUSAN寫信來了。」
將惠是不可能跟我回台灣的。她的父親一走,家中只剩下母親一人,我也不忍心置她於一個兩難的境地。
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節前夕,她排除了萬難與我在橫濱見了面,已成一個多月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她在住處將父親的照片以及她與父親兩人的合照翻出來讓我看。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一個同情中下階級的左翼運動支持者。「真是可貴的靈魂。要有什麼三長兩短,就真的太可惜了!」我惋惜地說。
撫摸著她的臉,我警覺地發現她瘦了,耶誕夜的淡妝掩藏不住她已消瘦的臉龐。「常哭?」我問到。她把相簿放到一邊,便將頭埋在我的懷裡,雙臂抱著我‧「KOUSAN,今晚不要談感傷的事,好嗎?」
我點點頭。我與她看著錄影帶,一個鐘頭下來,她盯著電視畫面,幾乎不曾看我一眼。大概是為了「宣示主權」吧,我主動地撫摸起她的身體。她在心理上似早有準備,自動將衣服一一褪去,,,,‧電視的畫面持續地播放與這屋內氣氛毫無關係的內容,螢光照在兩人的身體上,這個晚上,我兩比往常更快進入高潮。一番溫存過後,她終究忍不住,啜泣起來。看著她,直覺她想要說的,似乎已能猜得三分。「今晚過後,我們就不要再見面了。」她緩緩地道出這句久經沉默後的話。意在言外,也在言內。
「JYA,SOUSHIROU(好,就這麼辦!)」我的回答幾乎是脫口而出。她略為一怔。
「你不問我為什麼?」她望著我,眼淚再度不由自主地流下來。「我要留在川崎照顧爸爸。你人在茨城,我兩何時才見得到面,我不知道;你在校內,可以挑的對象那麼多,你真的認為我兩的感情可以維持得長久?…」
「這些都是次要的吧?」我打斷了她的話後,接著說:「妳母親的反對才是主因,不是嗎?」我單刀直入地闡明了我的猜測。
「不要想這麼多。」她丟下這一句話,不再多作補充,淚珠則任其留在臉龐。
我幾乎無法等到天亮。在她百般請求下,我才勉強留在她的房內,翌日,我整理好衣服,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便頭也不回的離去了。
自大學以來,自認在情場中已是身經百戰了,但這一次的離別竟讓我有如刀割般地難受!我回到家中,聽到她語帶哽咽的電話留言,已無法再裝瀟灑,恣意放聲大哭起來….。將惠的父親過世後,我們曾見過一次面。直到我離開日本前,不曾再見過她。去年我開始人生第一份工作,五月奉派到日本出差,與她重逢。她已經有了個男友。「到現在,我現在的男友依舊忌妒我與你曾有的那一段。」她苦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