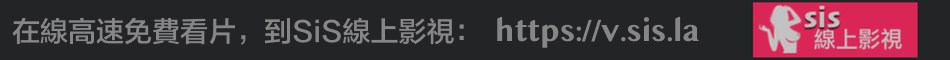我和公公的往事
我說:「我讓你買你就買呀,這麼聽話呀。」
公公好像有些不高興了,唉,我給他開玩笑呢。看來這人老了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
我忙哄他說:「今兒就由著你盡著興折騰,好不好?」
終於麻繩上了我的身子,公公捆得很緊,麻繩勒進了肉裡,我的身子像著火一樣發燙。最不能忍受的是公公這個時候摸我的陰部,讓我的下面濕了一片。我吃驚,怎麼會對繩子這麼敏感。
一連幾天,那種麻麻漲漲的快感縈繞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我是不是變壞了,變得淫蕩了。我問公公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公公只是嘿嘿地笑。
「你有反應嗎?」我問他,他說有。
我又問:「以前你也經常捆綁婆婆嗎?」
半晌公公說:「當年你媽曾說把她教唆壞了。」
公公的話再一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起公公說過的少時對不起老伴這句話。我問公公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沉吟一會兒,說起了那段往事。
六十年代,大西北勞改農場缺管教幹部,公安系統從內地抽調了一批人員去充實。公公那時候二十來歲,血氣方剛,就自願報名去了。
想想也是,那個年代人單純,響應黨的號召,不是有那麼一句話嗎,哪裡需要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公公說他這一去,一幹就是十多年。
勞改農場的犯人基本上都是內地押送過去的,哪的人都有,什麼樣的罪行都有。
公公所在的武裝連不直接管犯人,只是負責外圍的保衛工作。如果有犯人越獄逃跑,他們負責追捕。
勞改農場的活很重,開荒、脫土坯、挖水庫、修水渠這樣的重體力勞動全由犯人承擔。
一天十多個小時幹下來,人都快要累得虛脫了,而犯人的伙食又很差,一頓兩個包穀麵饃饃,一碗白水煮的菜。
由於缺油水,總覺得餓,很多人營養不良,面黃肌瘦。
犯人裡面有老實的,也有不老實的,對付那些不老實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拉出去揍一頓。
因為怕被報復,管教幹部不參與打人,都是交給武裝連來執行。三、四個人事先在小屋裡等候,待犯人帶到一進門,就用麻袋套住犯人的頭,再把人吊在房樑上,用武裝帶抽。
公公說他們打人都打出經驗來了。吊人的時候,會讓你的腳尖離地面似著似不著的,就是為了增加受刑人的痛苦感。打人的時候,不傷皮肉,都是內傷,讓你外面一點看不出來。
勞改農場生活單調枯燥,更多的時候,公公他們只是拿犯人取樂,尋刺激。把人剝光了衣服吊起來,在雞巴上墜上秤砣,用不了半個小時,犯人就乖乖的求饒,服服帖帖了。
不久文革開始了,串聯、造反、奪權,搞得到處亂哄哄的。
一次,外地的某個造反派組織鬧武鬥,打死打傷了不少人,當地公安就抓了他們幾個頭頭,其中還有一個女的。
還沒等審訊,外面就鬧起來了,把公安機關圍得水洩不通,說不把人放出來,就要衝進去搶。沒辦法了,連夜把他們押送到武裝連關了起來。
公公說,其實那個女的一點都不漂亮,長得五大三粗的,而且態度很惡劣,撒潑罵街,一看就是個潑婦。
公公他們哪受過這個,就商量著怎麼整治她。以前都是整犯人、還都是男人,這次整女人,自然會讓他們更開心、更刺激。
到了晚上,把那女的弄進小屋裡,也不給她套麻袋了,反正黑著燈,只是借著窗外射進來的月光,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摸樣。
堵上嘴,扒了她的衣服,光溜溜的吊起來。那女的繃直了腳想夠地面,試了幾次,也就是腳趾尖剛剛著地,沒幾分鐘,她就痛苦地嗚咽起來。
黑暗中,男人的手摸向她的乳房和陰部。公公說那女的乳房大得嚇人,耷拉在胸前,摸上去像個布口袋。
即便這樣,他們也很興奮,好歹是個女人,總比母豬強吧。
公公的手一路摸下來,到大腿時感到一片滑膩的東西粘在手上,一聞,一股男人精液的腥味,也不知是誰憋不住手淫噴上去的,自己也不覺得下面有些翹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