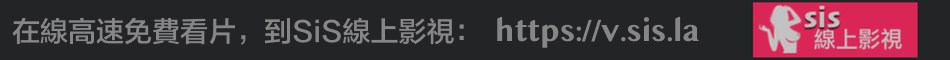初夏的遊戲
秋瑛聽了不服,打了我臉上一下,道:「白牙斬斬,看你也不是和我一樣嗎。」 說著說著還用劃著臉對我再說下去。 「羞….羞,看你這寶貝兒,殺到滿身傷痕現在縮頸藏頭,不敢見人了,難為你也。」
見她還說得出此種風涼話來。 我見她這樣情形,也就對她說道:「秋瑛,不要多說了,現在閒話小敘,言歸正傳了,秋瑛妳昨夜對我說的事,趁此大家都筋疲力竭的時候,兌現了吧,也由我聽得自自然然好了。」
秋瑛聽了我催促,她一說她的失身往事,很幽怨似的道:「洪哥還是少說了罷,這令人傷痛的追述,說了起來,甚為難過。」而且投入我懷中,輕輕的吻著她的臉兒道:「當我在剛巧十五歲那年,我們全家人都在家鄉居住,那田家樂的日子,倒是過得安靜和快樂,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習慣,我自在的過著,雖然我全家的人,只有父親和我母親,與及我的九歲弟弟而矣,我父親在家鄉裡,可稱得上是小康之家,不愁衣穿住食,倒我是全家和氣快活。
「弟弟在埔心村的小學裡讀書,我則上國中,平時跟母親學習女紅,與助母親廚房的工作,似這樣的家庭,在鄉間裡,無須終日聯手胝足的終日在田中工作,我可說是天堂與地獄之間,但是物極必反。」
「就在這年的夏天,我的母親竟然染上了流行病,死去了,禍根從此就種上了,母親的百日過後,就有很多之淫媒來說我的父親娶填房娘,當時我的父親已經回絕了很多,但經不起日久的浸淫,及生理上的需要,卒之娶了鄰村的一個已婚孀婦作填房。」
「初時返來的時候,倒能待我姊弟二人有些好處,及至日久,她的原形,也就現了出來,這時父親因為和友人合股在高雄做生意,不能時常的在家,她本是一個極端淫蕩騷浪的婦人,不慣獨宿的,父親既然不能在家與她長敘,每月只有回來一次或二次而矣,她本是夜裡無郎君睡不著的人,看我姊弟二人年幼,竟瞞了父親,招接往日未嫁過來我家時,與她私通的姦夫,公然上門來我家,對外人則說是她的姑媽的兒子,也是她的表兄,現由遠處來探視她的,公然接他在家裡居住在左邊的客房間。」
她的姦夫在這住了十多天,父親也回來了,對他客氣得很,還對他說,既然遠路往來不便可以在我家中住長久一點日子,然後在歸去,以免跋涉,隔日父親也就照常南下高雄去了。
隔日她的那位表兄,說要帶我及弟到台北玩,但弟弟要考試,只帶我一人北上,說好順便幫她帶一些胭脂粉類,我的後母高興的不得了,出門前還特別交侍要早點回家。
誰知一到台北,他說有點累,想先休息一下,帶我到旅社便開了一間房間,當我一進到房裡他的真面亦表露無疑,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來台北是借口,真正目地是要佔有我強暴我的身體,說什麼太久沒有玩玩幼齒的,我呢?剛好可以免費的長久來滿足他,因那時我身材算是同年齡中早熟了些,乳房發育特別好,那時胸圍就有32吋大,腰圍24吋,臀圍35吋,臉旦長也蠻標緻,所以當他到我家中那天起就一直打我身上的主意,今日終於被他等到了,由他身強體壯,以我這一介弱女子那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沒三兩下功夫時間我全身的衣服就被他脫的脫,撕的撕,就連最後一件三角褲也難逃一劫被撕成兩半,我當時兩手不知要遮乳胸還要遮下陰戶,只見他自已脫光衣服,下面的陽具是粗大無比,第一次看到男人那支大陽具足足有七寸長,紅的發紫,漲滿著,且又高挺,當時真害怕,我那小小的陰戶容得下它,一時心慌想跑出去,但被他那強而有力的手捉回來,一手就把我往床摔過去,人就暈過去。
昏昏沉沉中只感到陰唇顫抖不已縫裡似人淚滴,而喉頭奇乾,嫩穴一幌幌的磨著,騷水也潺潺的向外猛洩,有如似逢狂風暴雨一般,被逗得淫亂饑渴的驚醒過來,我連忙要推開他,但他越緊抱著我,他另一隻手撫摸我的全身,最後他用從我身上撕下的衣服將我雙手捆綁,然後由頭至腳的打量,我一身細皮白肉是那樣美而標緻,高誓乳峰柔軟光滑,圓屁股白裡透紅,紅裡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