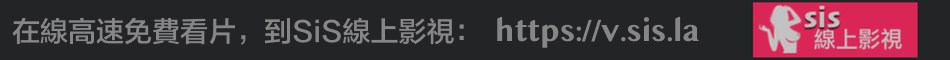被強上的女戰士
- 分頁 1 /8
- 下頁
老人躺在床上,附近牧場人剛剛離開,他們有的叫他胡裡奧大叔,有的叫他胡裡奧爺爺他們是來給他送行的,也許明天,也許還有一個星期,他就會死去,癌症已經在他體內擴散,腦癌,肝癌,還有前列腺癌,三處癌都是原發性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了。
60歲的老廚娘瑪麗亞,挺著依然如水桶一般的腰,輕輕的走進房門,道:「老爺,吃點什麼?」胡裡奧搖搖頭,歎了一口氣,「把針劑拿來。」針管裡是兩毫克馬啡,老人熟練的把針劑推進自己的血管,閉上眼睛,享受著片刻間的幸福的感覺。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麼?所有的不動產都分給了鄉親們,現金全部給了瑪麗亞,無兒無女的他可以安心的,帶著所有的秘密走進地獄了。
門鈴聲響了起來,噢,對了,他還有最後一次的和一位不相識的人的見面,對方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女作家,他不知道為什麼這位女作家一定要來拜訪他這麼一位默默無聞的阿根廷農場主,但是他喜歡她的聲音。「她一定是一位二十七八的金髮美女」,他想道,他希望把這場見面安排在他的生命的盡頭。看著一位美女,在溫馨的交談中死去是應該符合他這樣一位第三帝國黨衛軍中校軍醫的身份的。
「您好,卡洛斯先生,終於見到您了。」果然他見到的是一位容貌比她的聲音更美的青年女子。筆挺的灰色套裝,乳白色的細高根鞋,肉色的絲襪。「一定是連褲襪」,老人以他的經驗判斷著。
「您好,史密斯小姐,很高興見到您,我這附樣子讓您失望了吧?」
「怎麼說呢?您的氣色要比我想像中的要好。」
「哈哈哈,您恭維我了,請坐」老人喘著氣「史密斯小姐,喝點什麼?」
「咖啡,您可以叫我安妮。」
「瑪麗亞,來一壺咖啡,如果我不搖鈴,你就不要進來了。」
「您想知道什麼?」
「我想,在我正式訪問之前,先請您看一段錄像,可以嗎?」安妮說完,隨手打開了小型錄音機。
老人點了一下頭。
安妮打開隨身攜帶的筆跡本電腦,放入了一張光碟,畫面上是一個乾枯的老太婆,老太婆說的是俄語,屏幕下方是德語字幕,在淚水中老太婆不斷重複著一句話:「他們說我們是叛徒,可我們怎麼可能是叛徒呢?」
安妮暫停了錄像,「卡洛斯先生,您認識她嗎?」
「她說的是什麼語?是斯拉夫語麼?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給我看這個的目的。」安妮沒有說話,用鼠標點了一下繼續,這時的畫面上出現了一位女軍人的照片,準確的說是一位蘇聯紅軍中士的照片,年輕,淳樸,帶著微笑。誰也不會把她和剛才那個老婦聯繫起來,可她們的的確確是同一個人。
胡裡奧。卡洛斯幾乎休克,在昏倒之前,左手指了一下針劑。
安妮給他進行了注射,胡裡奧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像癲癇發作。
「卡洛斯先生,噢不,舒爾茨先生,你的反應已經說明了一切了。」安妮的嘴角邊有一絲得意,「您可以放心,我不是莫撒德,CIA或者FBI的人,更不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特別任務執行人,我只是一個作家,我只想知到真相。」
舒爾茨很久才緩過氣來,「你想知到什麼?」
「一切。」
「從哪裡開始呢?」老人沉吟起來,「好吧,我就從戰前開始吧。」
舒爾茨舔了舔嘴唇,我是1938年畢業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人類遺傳和生殖方面的,隨後就在柏林找到了一份工作,1939年,我加入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您要知道,安妮小姐,當時我並不完全贊同國社黨主張,但那時侯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我也沒有其他選擇。9月份的時侯,戰爭爆發了,可我總覺得那離我很遙遠,我是婦產科的醫生,任務是協助生命來到人間,和戰爭殺人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可是1941年2月,一道入役通知書放到了我的辦工桌上,我被命令在72小時以內到徵兵處報到,四月底,我們一整個野戰醫療大隊,被配屬到南方集團軍群的第11集團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