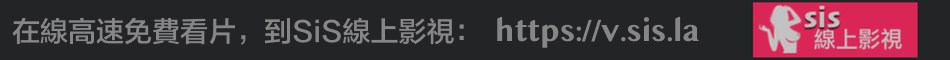夢花生媚引鳳鸞交
- 分頁 2 /2
- 上頁
酒喝得半醉,國卿裝醉問道﹕「賢弟美,姐姐更美,賢弟已肯讓我取樂了,你姐肯麼﹖」
花生只笑不語。
飲完了酒,花生扶國卿到床上,不免又幹起風流事,小官說﹕「小聲點,別讓姐姐聽見了。」
國卿說﹕「她聽了心裡不癢嗎﹖你姐姐寡居,我亦無妻,不如你做個媒人如何﹖」
花生說﹕「我難以敝齒,不如你自己去說。」
國卿說﹕「我亦難開口,實在是你姐太美。」
花生說﹕「也罷,我教你一個法子,明日我故意耽擱些時間,你自己在家裡用些功夫,成不成看你運氣如何了。」
國卿說﹕「萬一你姐翻臉,怎麼辦﹖」
小官說﹕「想她不會,一旦放手,哪有反悔的道理。」
第二天,小官同老僕人出去,國卿拴上了門,獨自在屋裡假裝看書。
巫娘進來,送了一杯香茶,國卿躬身謝道﹕「聽說大娘守寡多日,其是難得,只是那冷風苦雨,花前月下的時候,能不動情﹖」
巫娘說﹕「我已習慣了。」
國卿又調逗﹕「有一男子,和我一樣,在下做媒,大娘可願意嗎﹖」
巫娘說﹕「恐怕沒這個福氣。」
說罷轉身欲進家去。
國卿慾火按捺不住,心想﹕「看她意思像是願意了,不如大膽闖入,看她如何。」
巫娘正要走,國卿上前一把摟住,兩人撞了個滿懷,巫媳推他說﹕「不能這樣,快放開我。」
國卿不聽,抱起巫娘,放倒在床上,壓上去就嘴對嘴的把巫娘親了個快活,國卿見巫娘已媚斜了眼看他,知道時機已到,速速地脫盡她的衣服,也顧不得欣賞那一身水鄉女子特有的潤白皮膚,頂起玉蕭,從半空中狠狠地插入巫娘的蓬門內,驚得巫娘叫起﹕
「哎喲,從沒見過你這種架式的,下手太重,把人家扎狠了。」
國卿低頭不語,一心在床上用功,直把巫娘又插又拔地抽動了上百餘次,盡情撫弄了無數回合,直到上午,才累得挺不起來,昏昏躺到一邊去了。
小官回來,擺了酒,喝到晚上,小官裝醉,回到房裡睡去。
國卿摟起巫娘,坐到床上,挺出陽物,讓巫娘脫了裙,也對著他的臉,把花心對著陽物套下去,巫娘坐了一會,只覺得體內的陽物赤熱無比,她耐不住癢,套著陽物倒抽起來,不免嘰嘰地響,隔壁小官聽見,陽物也直豎起來,不免湧出許多黏汁來。
國卿與巫娘弄到三更,叫得也累了,兩人也快活夠了,一個抬不起頭,一個開不了口,於是抱緊了雙雙睡去。
第二天,國卿回到小官處,見他仍沒醒,於是又對著他的後庭花插去,抽動到極樂境界,像丟了魂似地昏迷睡去。
又過了一天,國卿要啟程,巫媳忽然猛叫肚痛,只好讓她暫看箱子,眾人提了行李先下船去,過一會又來搬箱子,國卿與老僕人一道上船,小官也吹起笛子,上得船來還沒有坐定,就見一人匆匆忙忙跑來說﹕「花生不好了,你姐姐痛得昏死過去,快回去看看。」
國卿也要與小官一道回,小官說﹕「相公的前途要緊,等姐姐好了,自然會去找你的。
說著跳下船,一路跑回家去。
國卿見小官遠去,覺得傷感,剛得到了一對美妙的姐弟,如今全都不在身邊。
船行約半個月,到達南京,在承恩寺租了一間僧房住下。
第二天打開箱子,準備取銀子繳納租金,國卿取出一封五十兩的銀子,拆開一看,竟是一對鵝卵石,頓時大驚說﹕「奇怪了!」
連忙又拆一封,也是鵝卵石,國卿臉都青了,忙把一箱的銀封拆開,全是鵝卵石﹗
老僕說﹕「難道說是夢花生和他姐姐調了包﹖」
國卿說﹕「本是個好端端的人家,不可能呀﹗」
老僕說﹕「那天他姐姐明明好好的,卻忽然肚痛起來,接著又把小官叫走了。肯定是他們合謀做的手腳。」
國卿想想有理,忙說﹕「不如現在趕回去,或許還能找回銀子。」
老僕說﹕「相公,那是不可能的,強盜拿了財寶,還會等你去尋找回來。不如相公好好用功,如考中了,可以光宗耀祖,別因為銀子耽誤錦繡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