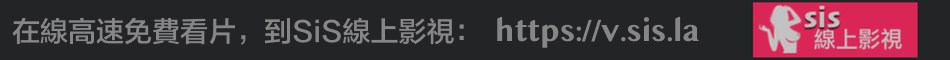小姨情深
她認真地說:「不要呀!外面那些地方那麼髒,你去洗一個澡,我來替你按!」
我笑道:「你會嗎?」
她說:「你忘記了我學完了物理治療,有按摩師資格嗎?」
這倒是真的,於是我就讓她試試,試起來也真舒服。我說:「你比芬蘭浴室的職業技師更好!」
她說:「即是說你常常去了?」
我說:「不是呀,上月才第一次去!」
她在我的肩上撻了一掌,怪責地說:「你真髒!」
我說:「怎麼了?按摩有什麼髒?」
她說:「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的治療導師之中有一個以前是在芬蘭浴室做按摩小姐的。她對我講過!」
她不出聲。我轉過來輕輕執著她的手:「現在我知道了,我也坦白對你講,女人之中,除了你的姐姐,我是最喜歡你的,我要再娶,一定娶你。」
她低聲抽泣起來了。我又說:「但現在你姐姐還在人間,我不能另娶,我怎能對你講呢?不過現在已講了,我們就什麼都可以講了,你想我怎樣對你呢?」
我又輕撫她的背。她靜了一陣才說:「姐姐也講過,假如她有什麼不測,我就要代替她照顧你,首先是解決你的肉體需要!」
我嘆一口氣:「肉體不是那麼重要吧?」
她說:「不重要你就不會去找女人了。我不想失去你,萬一你找著一個你喜歡的呢?還有那個嘉露呢?」
嘉露是我的女秘書,自我的妻子出事後她就經常有所暗示,怪不得她和芝珀一向都不咬弦;女人的本能使她們知道誰是情場上的敵人。而芝珀也講得有道理,她知道我與她姐姐的歴史。當年我們戀愛時,我有兩個女朋友,難以取捨,芝珀的姐姐很開放地和我上了床,另一個卻認為性是大罪惡,我便順理成章地娶了這個。
我說:「嘉露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我心裡的人是你呀!」
說著我就坐起來,擁著她吻她的嘴唇。她整個發軟,躺了下來,我擁著她吻了她的嘴唇好一陣,又輕吻著她的額。那股女兒香更濃了,一定是動情而散發的。這並不出奇,因為我也情動,我的陽具就已硬如鐵棍,而我相信她也嗅到了若干男人的氣味。我的心如放下了重擔,因為我已和她溝通,以前不知道的情感也發了出來。我想要女人又不能正式找女友,但她的姐姐有言在先,她就有如她姐姐的化身,我就可以不內疚。不過我馬上又有了另一副重擔:怎樣處置她?
我說:「我們該怎麼辦呢?我目前不能和你結婚,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
她說:「誰說結婚呢?眼前的問題先解決呀!」
我正奇怪她說的是什麼眼前問題時,她忽然一伸手隔著睡褲握住了我的硬挺挺的陽具。我有如觸了電,差點射了精。我深呼吸著忍著。她忽然又放了手,說:「好硬呀!果然是,你想射精了!真可憐,姐姐說你幾天沒有就坐立不安,你卻忍了那麼久!我用手來為你出吧!」
我有些發呆,我說:「你不是處女嗎?」
她說:「當然是了,但我聽姐姐講得多了,我還請那導師教過我呢!」
即使不是處女,一個女人也很難對一個與她未有過肉體關係的男人講得這麼露骨的。但我知這我這小姨的性格是怪怪的,有些很普通的話她會認為難為情而說不出來,但有些很難為情的話她卻可以毫無顧忌。不過,真的可以…..?
我說:「為甚麼用手呢?」說著我又擁住她,吻著她的嘴唇,既然用手也肯,何不真箇銷魂?我的右手按住她的左乳。
她忽然狂猛地一彈開,跌到地上,坐在那裡哈哈大笑。
我摸不著頭腦,拉著她的手要拉她起來,一邊問:「你怎麼了?」
她甩開我的手,還是笑著說:「不準碰我呀!癢死人了!不準碰!」
我說:「但是我吻你你都不怕呀!」
她說:「別的地方不要緊,那裡就不行!你要我替你出精,你就要聽我的話!」
真是怪人!她引起我的好奇心:究竟怎樣才合她意呢?我說:「不如任憑你擺佈吧!」
她說:「這就對了,你要聽話呀!先脫掉衣服!」
說著,她就爬上床來,跪在旁邊,很快就脫得我一絲不掛。她輕摸我的陽具。這倒使我覺得難堪了,因為雖熄了燈,還是有外間的光從外面透進來,我的陽具硬得一跳一跳的,她卻還穿著衣服,很不和諧的。
我說:「你也脫衣服吧!」
她輕捋我的陽具說:「我不過為你出精吧了,我不需要脫衣服。」
我說:「為甚麼要用手呢,我們索性造愛吧?」
她說:「又沒有安全套,下次買了才做吧!」
我大可以即時起來去買,但我覺得和她性交一定是可以的事,倒不如先行享受一下她這特殊的服務。一個從未經人道的處女為我手淫,這是一生難逢的經歴,於是我繼續任從她擺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