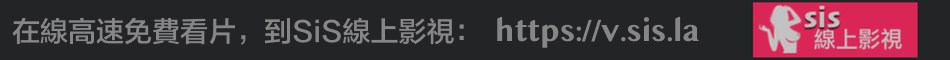夏日豔陽訴衷情
- 分頁 1 /8
- 下頁
約在四年前,我還是一位大學生,是大四的時候,我不住在宿舍中而在外租房子住。
那是一個新秋雨後的晚上,蔚藍的天空,明淨像洗過一般,幾點疏星默默伴著一輪涼月;我躺在涼椅上,對此寂寞的自然界,感著人生的煩悶很無聊的幻想著………….. 長了這麼大,還未涉足花街柳巷,只從朋友同學所收藏的花花公子,及一些黃色書刊中,約略明白男女之間的一些事,可惜從未嚐試過;我胡思亂想,毫無目地在花園走來走去,不知不覺已來到房東的房邊。
咦! 如狗吃水,嘖嘖有聲,我不由驚疑的停下來。
「哼哼!.. 快活死了! 親….心肝….我不知道了…. 」 一陣模糊斷斷續續的婦女叫喚聲。
「適意嗎! 癢嗎?….. 」 一個男子氣喘喘問著的聲音。
「適意極了! 好哥哥,你再重些….」
又是一陣吱吱格格震動的聲音,咦! 我感到很奇怪、很驚疑,一走近窗前才知道原來是房東夫婦倆人正在翻雲覆雨,我想自己既未嘗過這樂趣不知味道如何,今有這機會好不容易才能偷看別人在幹這檔事,便把紙窗挖破了一小孔,放眼一望只見室中燈光明亮,房東太太赤裸著身仰臥在床而房東張生財一絲不掛,立近床沿,掀起了夫人的兩條腿,正在那裡雲情雨意,他很有興趣的抽送了百餘次,便伏在太太身上一連接了幾個吻。
當他們興致正濃時,站在外面的我早已是全身渾麻褲子頂的高高的,甚至有點濕。
「心肝! 太太! 妳肯把妳的寶貝給我一看嗎? 」 生財一面接吻一面模糊的要求他太太答應。
「死人! 穴都給你幹了,還有什麼不肯給你看? 」 他的太太在他肩上輕輕一拍,表示十分願意。
生財笑嘻嘻的站起來,拿了檯燈蹲了下來,把那陰唇仔細端詳,他的太太更是把雙腿分開,站在外面的我,只見黑漆漆一撮毛兒,中間一條小縫,好不奇怪呀! 生財忽然張開了嘴,把舌尖伸在陰唇中間,一陣亂舔亂擦,不用說他的太太騷癢難當,就是站在門外的我,也覺垂涎欲滴,不知其味是甜是辣,是酸是鹹,恨不得衝進去分他一杯。
他太太被他舔的,只見縫中流出白色的淫水出來,在癢到無法忍受時忙叫生財將雞巴插進去,全根盡沒,生財用力抽送,他太太哼哼不停的呻吟。
「心肝! 為何你今晚這般有興呢? 」 他夫人很滿意的說。
「妳大聲浪叫,我再弄的妳更痛快。 」 生財笑著說。
「啊呀! 你插死我了! 」
他太太果然大叫起來,生財亦是很賣力的抽送,一連抽送幾百回,他太太漸漸的聲音低下,眼睛才閉了,只有那呼呼的喘息聲。
我這時再也站不住,只得握住下面堅硬直挺的陰莖,一步一步,難受的走回園中,坐在椅子上,滿腦子全是剛才那一幕活春宮,滋味究竟如何使我這在室男難過異常。
這夜翻來覆去,心神難安,老想著那一幕,那陰莖也奇怪的很,老是高高挺起,久不復原,最後沒法就手淫了一回,才將那陰莖打消了。
原來張生財是個木匠,今年年初剛結了婚,和他的新婚妻子買了這一棟房子,由於房子大,加上靠近學校,所以就讓我租了一個房間,住了進來。生財是個粗魯的男子,滿臉土氣,他的太太,卻生得花容玉貌,眉如山,眼如水,真是「癡漢偏騎駿馬,美嬌娘伴老頭 」 。
生財每天早上八時左右出門,通常到晚上九時左右才回來。白天只有他的新夫人一個兒,我有時碰見常叫她張嫂嫂,她都叫我錫堅弟。
由於上次看了他們夫妻玩了一次之後,我常翹課回去,那房東的臥房我平時不常去,現在有事無事每天必光臨幾次。白天常常藉機與張嫂嫂談談笑笑,無非藉機親近,到了晚上,又跑去看他們演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