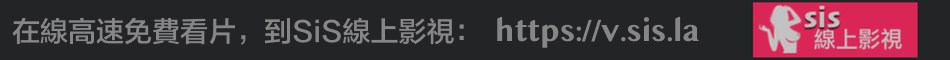年輕村寡赤裸裸的風流事
芳姑覺得自己如站立在茂密的枝頭,腳下搖擺,伸手能夠到天。她眩暈,似被白白的雲彩托在空中,飄蕩於浩瀚藍天裡。是的,就是這樣,她覺得到處一片白,白茫茫的視野,白茫茫的神志,白茫茫的靈魂。
她渴望這種白,從丈夫死去後,她就幻想這樣的白,也在等待這種白。那天當在大棚裡朝此刻身上的男人脫去她身上僅有的三兩件薄衣時,她就知道,饑渴等待幾年的白,終於又將籠罩在她身上,鑽進她體內。
男人感覺到體下女人突然大叫了一聲,隨之她一陣急速顫栗,同時無語地兩手死死摟緊他,兩腿緊緊夾住他。他感覺她那裡更滑潤和粘稠了。他是個很懂性的男人,也體諒女人,於是沒有再動,而是讓女人靜靜享受發子體內的脈動舒暢。此刻,他清楚,下一個沖擊波,該輪到他了。
果然,幾分鐘後,芳姑汗粼粼嬌喘地說:死人,好了,過去了,你再來!你咋這能呢?
於是男人重新振作精神,像個勇士拿起武器,發起最後一輪沖擊。這一次,他是為自己沖鋒。
十幾分鐘後,在芳姑比上一次更加狂猛的喊叫聲中,在女人的軀體緊張夾裹中,男人把自己徹底放棄,同時,他發出幾聲低悶的哼聲。隨後兩人如剛出浴般,都閉著眼躺在床上,大口喘氣,一言不發。
男人的呼吸平穩了,女人的胸脯也不鼓脹了。暴風雨後的平靜,熱浪翻滾後的安詳。
芳姑翻身從床頭櫃抽屜裡拿出煙和打火機,抽出一隻香煙,遞進男人嘴裡,啪地一聲打著打火機,幫男人點上。男人嘬了口煙後,把煙從唇上取下來,看了看,立即一臉驚訝地問:你咋有這高級煙?
還是不為你,俺最膩味煙味了,可你完事總喜歡抽,俺好像也喜歡你在俺床上抽煙,俺就為你買了。是昨兒晌午買的。此刻女人趴到男人胸上,一隻嫩白小手扶弄著男人的細小乳頭。她喜歡這樣摸男人。
別弄,癢,難受。男人扒拉開女人的手。
男人很快抽完煙。他一翻身,壓在芳姑身上。芳姑欣喜,以為男人又要來。可是男人卻拿過煙盒,看了看,發現裡面煙少了好幾只,不像剛開包的,於是問到:咋?你給過旁人這煙?
是,昨天有人來了,抽了兩只。芳姑囫圇回答著,同時手緊緊抓住男人下面。她還想再來,這個男人上她家一次不容易,而且還讓她這麼舒心,所以她胃口很大。
是哪個來了?男人立即警覺起來。
問啥啊?沒正事,村上來收水費,去年的水費俺沒叫,他們來催俺。芳姑加快了手裡的動作。
男人沒有阻止芳姑扶弄自己。不過,他想弄清楚誰來芳姑家,於是繼續問到:到底是誰?告訴俺?不會是三賴吧?他可是個流氓。
三賴是村裡的二流子,一向好吃懶做。他還有個很糟人恨的鬧病,專愛佔大姑娘小媳婦的便宜。他常給村裡出難題,先後幾任支書和村長拿他都沒辦法。後來,現任村長李大全使出一高招,把二流子招進村後勤組,讓他負責村治保,每月給三頭二百。村裡出現比較難處理的事,像收電費水費的、計劃生育蹲坑盯哪家小媳婦等等,村長就會派二流子去。
聽到男人的追問,芳姑的臉通紅,她猶豫了一下後低聲說到:他來沒做啥,就是收水費,俺沒給他。
他真對你沒做啥?俺不信。告訴俺,到底他咋沒咋著你?男人急了,攥緊芳姑的圓潤胳膊,瞪著眼睛問到。
看到男人這麼在意自己,芳姑如吃了蜜一樣,心裡很甜,可是,想到昨天三賴那樣對她,她又感覺渾身不自在起來。後來,她諾諾地說:他對俺……就對俺…。
於是,芳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把三賴昨天在她家做的事,哭著向身邊這個男人,說了出來。
女人說到:昨兒晚上俺剛吃過飯,三賴來了,找俺要水費。俺不想給他。他威脅俺說不給錢他就不走。俺求他幾句,還拿煙給他抽。可他心好壞,就是不走。後來俺急了,跟他說,俺要睡覺了,轟他趕緊走。
在俺往外推他時,他要親俺,俺不讓,後來俺和他抓撓起來,他把俺的衣服撕扯了。說到這兒,芳姑朝窗下椅子上瞄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