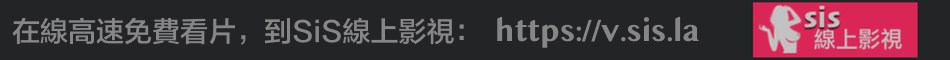母親的精力
很快聖誕夜到來,都12點了母親還睡不著胡思亂想著,她想起了朱赫來在去年聖誕給她創造的奇妙感覺,但她很快就開始自責起自己的褲帶太鬆了,如果自己自重一些不留下和朱赫來過夜,也許就不會受那地獄般的煎熬。她懊惱起來,只穿著絲絨睡衣就到客廳裡看電視以轉移思緒。她反對我吸煙,這時卻點燃一根香港朋友送的高級女士薄荷香煙抽起來。
我看見客廳的燈亮了,就爬起來到客廳看看,我知道母親為什麼鬱悶,就坐在她身邊想陪陪她,讓她高興起來,母親把身子靠在我肩膀上,一股成熟母性的氣息浸透了我的關節,我又感到了心中無以名狀的躁動,欲抱母親的腰,母親敏感地躲開,她沒有打我,而是輕聲而嚴厲地說:「孩子,你的念頭太危險了,這會影響你的未來,別對媽媽有不好的想法,這是犯罪呀。」
我從來不敢頂撞母親,此時大著膽子反駁:「勞倫斯說過,母親是男孩子在男歡女愛方面最好的導師。我實在無法忘卻媽媽,何況你也需要男人的安慰。」「沒大沒小。」母親又露出慍怒之色,站起來回房間了。
第二天我突然病倒了,高燒不退,也許是前夜只穿著短褲就到客廳裡坐了半小時著涼的緣故。母親很著急,寸步不離地照顧我,晚上我還頭疼地起不了床,母親怕我的感冒轉成肺炎,就在我身邊躺下好在夜裡看護我,我在迷迷糊糊中感到了身邊母親溫軟的身體,頓時清醒了一點。母親疲乏地打著盹,我拉開她睡衣的帶子,把頭深深埋在母親的雙乳之間,母親醒了,她也許是憐憫我,沒有責怪,縱容了我的無禮。我用臉蹭著母親的乳峰,又得寸進尺起來,把手向下面伸去。母親一驚,阻止了我的前進。我的手執意向前,母親說話了:「現在不行,你還病著,別胡鬧!」我聽話地縮回手愉快地睡著了。
1988年12月31日的晚上,妹妹在美國,又是我和母親在家準備迎接新年的鐘聲。我們娘倆伴著新春音樂會中「藍色多瑙河」的曲子跳起了三步舞。葡萄酒把不勝酒力的母親的臉襯得通紅,她歡快地應和著我的舞步,我忽然發現母親的高乳隨著我的旋轉也在劇烈抖動著,我的心潮又澎湃起來。
我有意識地和母親貼近了,我的胸脯隨著旋轉摩擦著那對高乳,母親不知道我是故意的,沒加理會,我把右手從母親的腰上向下移,在母親的豐臀上輕浮地撫摸。這下母親看出了我的不懷好意,她停下腳步瞪著我。我用雙臂緊箍著母親不放,嘴在她的脖頸上吻著。她喊著:「你怎麼敢欺辱媽媽?」我說:「我病的那天,你答應的。」「我沒說過。」
我不管她的辯解,把手從她西服裙的後面伸進去抓撓她臀上厚厚的皮肉,我那天的力量出奇地大,她的臉更紅了,但掙脫不開,似乎認可了:「好吧!好吧!我們到臥室去,看在你大病一場的份上,獎賞你一次,下不為例。」
她不好意思讓我幫忙,執意自己脫,她慢慢地脫去衣裙,我在旁邊看著。母親已是46歲的女人,至今細皮嫩肉,但決非文弱,有一副在女人堆裡算是偏高的健美身材。她的膀臂渾圓有力,她有一雙粗粗的結實的小腿,腳板寬寬大大,這是她年輕時酷愛打球和游泳的結果;她包著粉色三角褲的臀部肥厚圓滾,穿在身上的褲子時常被繃得緊緊的,讓人暗暗擔心它什麼時候會突然被撕裂;哺乳過兩個孩子的奶房仍高聳著,充斥著彈性。
母親進了被窩,我也脫得溜光拉開母親的被子鑽了進去。 我從沒和女人作過愛,甚至沒見過真女人的裸體。但我是法律系科班出身,學「婚姻法」的時候我認真鑽研過人類的性行為,正規讀物上的知識抽像有限,我從同學那裡借來地下書刊仔細閱讀,認真思考女性的性心理和生理特點,所以雖然是頭一次接觸女人,我還是有信心。
我背朝上趴著伸腦袋去和母親親嘴,母親羞得扭過臉去,她可能心裡還有思想包袱,不能進入狀態。我用雙手按住母親的頭,使她躲閃不開,用嘴包住她的熱唇,盡情親吻。我知道,女性的性反應遲於男性,何況是母親這樣的中年婦女,必須為她作好準備工作,否則她不滿意就不會有下一次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