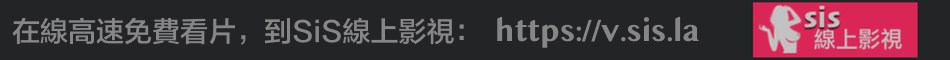紅色歲月的媽媽
我蹲下來,小心地一顆顆解開女人上衣的扣子,然後把衣服往後退到她的手腕處,象執行一次神聖的儀式。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小心,彷彿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是的,能有機會為組織為毛主席做一件事,是很光榮的,但是這小心的本身是否也意味著對敵人的尊敬呢,這簡直是犯了立場錯誤。於是猛地粗暴地將女人的背心拉起,由於用力過猛,竟然一下子將前襟扯了下來。於是,我看見女人的兩只乳房一下子彈跳出來,象兩只牛眼向外突著,直愣愣地看著我。我伸出手來捏捏這奇怪的牛眼,覺得很舒服,象忽然找回了一件失落多年的舊物。
禁不住將嘴湊了上去,用舌尖舔了舔,然後狠狠地吸了一口。嗓子空空的,沒有奶,這是與童年想的最大區別,但是,似乎有一縷香氣吸引著我,淡淡的,讓我不願松開嘴唇。頭有點暈,我覺得自己象是被什麼東西牽引著,在向下滑,直滑到漆黑的夜,然後又徐徐向上升騰,向著刺目的白光。耳邊是綠色的林濤和風聲,我自由地滑翔著,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在乾什麼。也許,一切都不重要。
我榮幸地受到了紅總站司令的接見。司令說:「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讓你負責監督看管那個臭女人賈美蓉,你能完成任務嗎?」
「能!」我兩腳一靠,興奮地敬了一個軍禮。
我的外祖父大約是個商人,在亂世中賺了一點錢,不算很富有,卻不願再回鄉下,娶了姨太太買下了這院房子來住。而這房子在他來之前不知道已經存在了多少年。可以想見我的母親在這房子中慢慢地長大,然後是外祖父被抓,杳無音信,然後遇到了父親,然後是我的出生和母親的遠走,我和父親相依為命在這座房子中生活,一直到他得病去世,從小候起,我就喜歡幻想被母親抱來抱去的,在她柔軟的懷抱中游弋,她的乳房堅挺而暖和,尖尖的乳頭是漂亮的紫色,我的手指常在那裡玩耍,它是我童年的記憶中最初的樂趣。這種樂趣一直持續到十五歲,也就是說,十六歲以前我一直沒有享受著別的孩子早已享受多年的樂趣。那時我的手指已經長得足夠長,可以毫不費力地抓住一個女人的整個乳房。盡管任誰要抱起我已經是很吃力了,但我還是幻想她仍然要將我抱來抱去,她抱我的時候我總要興奮地伸手去抓她的乳房,有時候彷彿是我把她捏疼了,她的身體便有了輕微的顫栗,臉上則顯出淡淡的紅暈來。這時她終於被我抓住了乳房,盡管是在那樣的地方!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十六歲,由於接受了紅總站看守賈美蓉的重任,學校決定獲準我提前一年畢業。十六歲的我,由於接受了偉大的政治任務而獲準提前畢業,使我具有了無上的榮耀;更主要的是,我可以從此不必去上學了,從而成為了一名正真意義上的紅衛兵。從學校出來,我把書包高高地拋向天空,然後奔跑著穿過街道,連家也顧不上回,一路跑著來到我家。見到我的媽媽賈美蓉,此時她是我的囚徒。此刻,媽媽被反綁著雙手坐在椅子上,怒目而視。她衝著上氣不接下氣的我說:你這個流氓,我恨不得吃了你。我高聲嚷道:不許亂說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為自己現學現賣的樣子很滿意,覺得自己已經具備了一個革命者的素質。但是接下來該做什麼呢?我站在那兒想了半天,突然靈機一動,激動地高舉著雙手跑出去。
整個下午,我都忙得不可開交。找來一大捲大字報貼滿了兩間屋子所有的牆壁,正對著媽媽的牆中央貼上了一張毛主席畫像,底下是我親手寫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看好賈美蓉,保衛毛主席。」待到所有的這一切都做完,天已經很黑了,我站在角落裡欣賞著自己的傑作,忽然感到飢腸轆轆,他想,革命者也還是需要吃飯的,人是鐵飯是鋼嗎?他走出屋子,不放心地回頭看了賈美蓉一眼。
而我媽正面露微笑望著我。
夜色來臨了。在那個夜晚我完了。我早晚會栽在自己手裡。
又是午夜。黑暗是罪惡的衣服。
我躺在床上。醞釀著勇氣。我緊抱著枕頭。彷彿摟住她嬌小的腰肢。及至幻想如烏雲般在腦海里展開。我不再猶豫了。我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門襟輕松地往一邊撕開,給她打開銬在身前的雙手,順帶著把她的手臂反擰到身體背後。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飛了她腳上的布鞋。轉眼之間她身上的衣服連同內衣全都被從身後撕扯下來扔到了屋角里。我又給她反剪在背後的手腕哢嗒一聲重新鎖上手銬。轉到她身前蹲下,用廢電線把她的腳腕分別捆在椅子的兩條前腿上,順手拉掉她仍然穿著的白布襪。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僅剩的內褲,從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來。媽媽很驚慌地喊到:「小畜生,你要乾什麼?」我一下子有了惻隱之心,畢竟她是我母親,就算她再對不起我和毛主席。於是我給她喝了一杯早以放了安眠藥的水,她累了一天,再加上驚嚇,終於睡著了!我把她赤裸裸的抱到床上。望著床上沈沈睡去的母親,那股深藏在血液里亂倫的因子再度活躍膽子同時也大了起來……看著她安詳入睡的臉龐,我衷心的認為她像一個女神一樣……而此刻,我即將用自己的身體,那個在十八年前經由她子宮所孕育的生命,來佔有、侵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