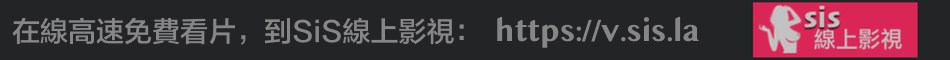我與岳母齊炒飯
「夠啦,你可真能吃,難怪那麼能……干。」說著紅了臉。
我拉過她來坐在我腿上,看著她慢條斯理地啜食,摟著溫香軟玉的軀體,心中油然產生一種……成就感,決心護衛她,讓她開心快樂。
「廚房裡有熱水,你拿到衛生間去洗一洗,渾身的汗臭味兒。」
我在她鬢間嗅了嗅:「你也好不到哪兒去,除了汗臭還有一股……」我故意拉長腔。
素愛清潔的靜靜果然急切的追問:「還有什麼味兒?」
我對著她的耳朵:「一股香騷香騷的味兒呀。」
「靜靜,你以前也這樣過嗎?」
「胡說!哪個能像你這樣,跟個…種馬似的見了屄沒命的肏!哎!可想起來讓你肏真舒服哇!渾身汗毛孔都通開了呀。」說著伸手抓著我的陽具撫摩起來。
「女人沒個男人滋潤著不行,你呀人年輕,傢伙也棒,又硬又燙的插進去,下下頂在花心上,舒服得腳趾頭都酥了!你還特能幹,肏一次沒四十分鐘一小時下不來,能讓人高潮三四回,真舒服透了。你從小就聰明,沒想到在這上頭也道道兒那麼多,才兩天呀,你就能把我玩兒的昏天黑地,再有一年半載的還不把人家玩兒的魂兒都沒啦!哪個女人讓你這麼肏一回不死心塌地的跟著你才怪!」
「對了,兵兵,我告訴你,和樺樺結婚以前不許你和她……發生關係,不是我吃……你太厲害了,她一個女孩子可受不了你!回北京以後隨你,在那邊可不行,聽見沒有?」
想到活潑可愛的樺樺,想到和她……早已在靜靜撫摩下硬了的肉棒倏地更加堅硬了。她也發覺了,嘻嘻笑著問:「怎麼又這麼硬啦,又想要啦?是想要我呀還是想樺樺呀?嗯?我可不敢再讓你肏了,這樣吧,姐姐安撫安撫兵兵。」說著掉過頭去,張嘴含住了我脹痛的陽具。
老天!還可以這樣嗎!
一股無可名狀的快感從龜頭『嗖』的一下沿著陰囊、會陰、小腹傳遍全身,一種說不上是酥、是麻、是癢、是酸的感覺充滿全身,彷彿起伏在波濤洶湧的享受的峰谷之中。
「嘻嘻,怎麼樣?你也受不了了吧!」她衝著我笑了一下又埋下頭去吸吮我的陽具。
她像吃雪糕那樣,反反覆覆地從上到下舔著棒身,時而又輕輕咬嚙著龜頭環溝,同時舌尖舔著馬眼,撩撥得肉棒跳動著幾乎洩精。然後她用溫暖的手掌緩緩地套動肉棒,舌頭轉而去舔弄陰囊,過了一會兒竟含住了一粒睪丸,我的腹肌隨著她的吞吐而收縮,她輪流吞吐著兩粒睪丸,最終把它們同時吞進嘴裡用舌頭按壓,一陣巨大的快感夾雜著輕微的疼痛襲來,我壓抑不住的發出聲音。
她用眼角瞟著我,那眼神分明是在說『怎麼樣?不行了吧!』。她又含住了龜頭吞吐起來,一隻手用力套動棒身,另一隻手輕緩地揉搓著陰囊。她吞吐的速度越來越快,短髮隨頭部的動作在空中飄蕩。快感愈加強烈,我提醒她:「喔!我不行了!要出來了!」但她並無避開的意思,卻加快了動作的頻率。
最後我無法抑制地在她嘴裡爆發了,一股接一股的陽精射在她口腔裡,她忙不迭地吞嚥著,但可能是太多太急的緣故,仍然從她的嘴邊洩漏出來一些。當我完全結束後,她舔淨了洩漏出來精液,並用力『嘖嘖咋咋』地吸吮著逐漸軟下去的肉棒,似乎希望要把我徹底搾乾,而我卻因為隨極度興奮之後而來的極度疲倦昏昏睡去。
從半敞的窗戶吹來習習涼風把我喚醒,這裡真是避暑的好地方,不管白天多熱,後半夜總有涼爽的山風順西面的山梁吹拂過來,帶著林間草木的清香將燥熱一洗而光。
她蜷伏在我懷裡,頭枕著我的胳膊睡的正香。明亮的月光灑進室內,藉著月光,可以清晰地看見她的鼻翼隨呼吸而翕動,曼妙的腰肢及高聳的髖骨也隨之起伏,胸前的碩乳亦微微地蠕動,好像月光照耀下乳波粼粼。
看著酣睡的靜靜不禁想起塞外的樺樺。小樺與她母親長的很像,無論眉眼面龐或高低胖瘦同靜靜猶如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只是樺樺膚色大約隨白伯伯而略黑了些,若她們站到一起說是姐妹也未嘗不可。在這明月當空的時候樺樺是在熟睡還是在思念我呢?可是我卻摟著她嬌媚的媽媽睡在一起!樺樺,希望你能原諒我,也原諒你的媽媽。
你的媽媽太美了!不僅漂亮而且熱情、溫柔,即便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她依然把你放在心上,為了你的未來而甘心與我保持這種不清不白的關係。她也真夠苦的了,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偏僻地方的淒涼恐怕你是不會理解的,我給了她極大的歡愉,而她更給了我難以名狀的幸福,畢竟她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女人!看她床上瘋狂的樣子和滿足後極度陶醉的神情實在令人難以割捨,假如你不肯原諒我的話…… 我一邊想著一邊輕輕地摩挲著靜靜。不知她何時已經醒來,見我始終在癡癡的思索著,便問道:「兵兵,這麼晚了你不睡在想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