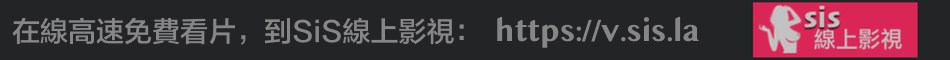美艷廚娘姐姐無奈與舅舅們周旋
我渾身癱軟地躺在床上,回味著剛才那欲仙欲死的滋味,感覺和先夫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可悲的是,正當我在自我陶醉時,臥室的門被突然回家的丈夫推開了。
看著赤身裸體的我,他失望憤怒地朝我吼道:「你這個不要臉的蕩婦!」,門被砰的一聲撞上,先夫隨後想用力拉了一絲不褂的我,出門遊街示眾!我光了大屁股呆呆地坐在地上,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不知所措,先夫的反應是如此之強烈,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篤篤篤,買糖粥,三斤核桃四斤肉,吃你的逼肉還濃的殼,張家老伯伯問我要只吃小黃狗的逼,今朝禮拜三,我去買洋傘,落特三角三,打只電話三零三,跑到喜馬拉雅山,屁股摜了粉粉碎」。
突然間,我想起我的父親,他能即興隨口編兒歌的本事遠近馳名,這和他幼年在大陸北方的成長環境很有關係。
北方農村的兒歌音調鏗鏘,言語詼諧,描述形象生動,聽過一次就能永世不忘。
我換個口音,捲了舌唱那首父親作的「誰跟我玩兒」,在華北長大的孩子都耳熟能詳。
小時候父親教我們唱,我加些色情讓男人樂樂 -「誰跟我玩兒,打火燫兒(注),火燫兒花,賣香瓜,香瓜苦,賣逼逼,騷屄爛,賣豆腐,豆腐嫩,攤雞蛋,雞蛋雞蛋殼殼,裡面坐著個哥哥,哥哥出來買菜,裡面坐著個奶奶,奶奶出來燒香,裡頭坐著個姑娘,姑娘出來點燈,燒了奶子和騷逼。」
唱完這一段,兩隻手就在自己身上和屁股縫亂摸一陣。
再來條「柳樹那柳」是俺那個村子的兒歌,就這麼唱:「柳樹那柳呀!槐樹那槐呀!槐樹底下搭戲台呀!人家的姑娘都來到,咱們的姑娘還毋來,說著說著來了!騎著匹驢,打著把傘,光著個腚(屁股),挽著個拶(音」鑽「,髻也),穿著雙套鞋,露著個腳尖,胳肢窩(腋下)裡夾著兩只大蒜肥奶碗。」
著實調侃起我這姑娘來。
一會兒我又換回蘇北小調,「阿唷哇,作啥啦?蚊子咬了我的屄呀,快點上來呀,上呀上了就勿庠。
一歇哭,一歇笑,兩隻眼睛開大炮,一炮開開到城隍廟,城隍老爺哈哈笑。」
「小雞雞,駕腳肏(發音是這樣),馬蘭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到了三十一,我大概是唱了太興奮了,體力不支腳也就站不穩啦,三寸細鞋跟被橡皮筋勾纏住逃脫不掉,一個踉蹌斜斜劃出了好幾步,這卻不打緊,糟的是我的肉甸甸的左大腳一弓竟然將姑姑的名牌高跟鞋給擠裂了!姑姑尖酸刻薄心狠手辣是有名的,這下我花容失色呆如木雞,感到背脊陣陣寒意,簌簌發抖!「媽的!……輸啦!鞋也被擠破啦!打死你這騷貨!」「要抽打幾下啊?就狠狠抽打你這騷屄二十下吧!」姐姐聽了渾身戰抖幾乎昏倒!,「啊,不……不要……那屄是要被打爛的啦」,我嬌喘著討饒叫道。
「那就改玩個成人遊戲吧,你蒙上眼脫光光,躺在椅子上,屁股擱在椅子邊緣抬高!來摳屄了!」我尷尬的隨即被蒙上眼睛剝光了全身衣物張開了雙腿,此刻我心中很明白,在婆婆家是沒肉可吃,要啃難以下嚥的硬骨頭了!熟女活到四十出頭還得被男人肆意性侵摳屄!「坐到椅子邊,把腿再張大一點!我們要仔細瞧瞧你的騷屄臭不臭啊!」婆婆弟弟用手拍了我大腿的內側,示意腿再要張開呈一直線!突然間,姐警覺到,有一隻手指卻趁機伸上挖進姐濕潤微溫的逼門裡,大拇指頭還頂啊頂,磨蹭姐的陰蒂;另一隻手指尖活生生地伸滑進我的菊花裡去ㄟ,奶頭也被摳捏拎起,連蓋在陰唇內的尿尿小孔都不放過被指甲尖端挑挖著開來!姐一蹙眉身子猛然一震就這樣被五,六隻手指肆意淫亂我的身體!無數的手指在我最敏感的部位遊蕩搓摸,我開始大口地喘氣不停的抽搐。
可是蒙了眼睛在這種情形下界不知如何躲避撩人慾火的攻擊,只能強行憋住氣抵禦全身傳來的令人酥骨的刺激。
姐的屁眼,陰核陰道酸癢麻疼難忍,那股酥麻猶如螫蝨噬心刺激不斷傳到小腹子宮全身內,一陣陣觸電般感覺從奶頭,屄心和直腸深處傳遍全身,連大腳丫板也刺激的再收縮綣起來。
身子連打了好幾個冷抖;喉頭一熱,心一蕩陰精,浪液,騷水睎瀝嘩啦啦地遺流出來ㄟ,從透明甘冽清澈到渾濁!半透明浪到流粘粘的奶油色,停也停不止!這些手指不停地偷襲磨蹭,頂呀頂住姐的屁眼,陰戶,奶子,每用指甲尖端摳一下,姐的身體就收縮一次,他們是好下流噢,還不停地移轉緊貼按住姐細嫩暴裂的陰蒂,一下重一下輕的磨蹭按揉,有時在屄心花蕾的皺褶上輕輕的畫圓劃過!他們緊緊地不放過這搔擾大好機會。